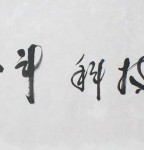| Article Index |
|---|
| 文怀沙的真实年龄 国学大师的荒诞人生 |
| 第二页--到底为何入狱? |
| 第三页 |
| 第四页 |
| 第五页 |
| 第六页 |
| 第七页--我们失去了文化判断力和敬畏吗? |
| All Pages |
三个疑点
这些年,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文怀沙先生频繁亮相于电视、报纸、网络各种媒体,故事越讲越生动,名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了。
在各媒体发表的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
事实果真如此吗?
1910年出生,还是192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作过的单位与呆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2。约1953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3.1963年底入狱劳教至1980年释放回原单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1921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1921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当年社会,尚无六十岁退休之忧,似不必把年龄说小。与如今的讲述相比,当年相对严谨的档案记录无疑更为可信。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88岁左右。
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
突出的一个光环:文怀沙多次自述中称章太炎是其老师,故与鲁迅是前后弟子。
据查,1934年秋天,67岁的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但在1963年文怀沙的劳教记录中明确写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如果他出生于1921年,1936年才15岁。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否继续办,文怀沙“肄业”的“上海太炎文学院”与之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同一学校?也有待考证。即便是同一所学校,也应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苏州迁至“孤岛”上海。按此时间推算,当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又如何见过?
另有一个光环:相关年表写到,1928年18岁的文怀沙,“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后任上海剧专教授”。按1921年出生计算,这一年他才7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身担此任。
由于年龄提前了近12岁,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就容易丰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记:“一九三八年 二十八岁秋,于重庆作《听雨》诗 :‘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亚子评曰‘诗出王摩诘而胜之。’”实际上,此时他还在上海念书,只有17岁,如何在重庆与柳亚子交往,得柳亚子如此嘉评?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飘动,步履轻盈,思路敏捷,皮肤滑润,已相当了不起,足可夸耀,大可不必多说一轮十二年。虚拟年龄,于天,于父母,似均为不敬。如果仅仅限于自家庭院,别说虚增十二岁,就是自称二百岁、五百岁,也是个人之事,不必较真。但是,如果以 “百岁”之假,行大做商业广告之实,对消费者无疑有误导和欺骗之嫌。一旦进入文化史范畴,人际交往与学术轨迹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细加订正,予以澄清。
到底为何入狱?
文怀沙的“文革”经历,特别是多年牢狱之灾,受他的自述影响,媒体的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故事神奇,绘声绘色,被渲染为英雄般的壮举。
关于其入狱原因,一篇报道说:“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 另有一处报道称:“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
这些叙述都不符合史实。
首先,文怀沙不仅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表现得十分积极与激烈,吴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对人说过,他对在“反右”中最不能原谅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剧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与文怀沙同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作为“吴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忆说:“在1957年批判吴祖光和我的大会上,文怀沙表现得非常积极,慷慨激昂。他指着吴祖光的鼻子说:‘你就是现代的西门庆,专门玩戏子。’他这是拿吴祖光与新凤霞的结婚说事。当时把我们气死了。”(2009年2月10日与李辉的谈话)
其次,所谓“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1974年因‘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的说法,同样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其它原因。
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1963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90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改。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由此可见,“文革“期间文怀沙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也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关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经历,叙述得最生动的莫过于写藏锋诗“反对江青”的勇敢之举。这一故事的版本甚多,大同小异,取其中之一如下: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梁效”这个名字,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帮“四人帮”说话、发表言论、攻击对手的写作班子,正好梁效写作班子缺人手,一个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让文怀沙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这个朋友将会帮助文老结束监禁和劳改生涯,并且可以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文怀沙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到西北,希望儿子能够在绝境之中服个软。文怀沙那时正在生病,躺在炕上,望着母亲蓬乱的头发、消瘦的面容,心中万分难过,但他还是说:“妈妈,我不能写啊,我不能违心啊。”母亲没有再说下去,只是叮嘱儿子别往枪口上撞。当时文老满怀心酸地点了点头,但没过多久,文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连起来读乃是“龟主江青”。当时江青看后随手就把这首诗扔到了沙发上,可能觉得没什么,这一点却被
王洪文看出来了。
故事实在太生动了!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让人生疑的是,按照当时他的处境,即便真有此诗,又如何能到达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将之“扔到了沙发上”,她没有看出这是一首“藏锋诗”,王洪文反倒看出来了?
关于这一“英雄”般的吟诗行动,徐晋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见闻录》中有云:“又谓其在狱中拒入梁效,且报以诗云……此诗每句第六字连读,则为‘龟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悬于文家书房。然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历史也。”
我赞同徐先生的判断。层累历史固然可以为编造者增添光环,但我们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们的在天之灵?
李辉:我为什么要质疑文怀沙?
自2009年2月18日《北京晚报》刊发《李辉质疑文怀沙》(拙文原题为《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他》)后,不少网民和记者都一再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现在要写这篇文章?”人们想知道,我忽然发出质疑,是否因与文先生有个人纠葛所致,文在视频谈话中,也编造一套我曾在狗年采访过他的说法,试图将我的写作动机暗示为人际恩怨所致。人们还想知道,我公开质疑,到底是想“一鸣惊人”,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因此,为使媒体同仁和公众有更深入的了解,我有必要将自己为何决定质疑文怀沙的历史缘由、写作动机和文化思考详加叙述如下。
一,二十五年前熟知其人其事
关于文怀沙先生的行状以及入狱原因,我不是因为突然间心血来潮,好奇所致而想到去挖掘,而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晚报》工作期间,就已经对此熟知,迄今已超过二十五年。
1982年初,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先是担任文艺记者,后任副刊编辑。同年夏天,王戎先生从上海来北京,要我陪同他去看望一些老朋友。王先生是我的老师贾植芳先生的朋友,四十年代在重庆从事戏剧运动,五十年代曾被打成“胡风分子”,我在上海念书时就与之熟悉。在陪他去看望胡风、路翎、牛汉等先生之后,他说:“我再带你去看几个戏剧界的朋友,你在北京以后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忙。”
我们先去看了凤子、沙博理夫妇,然后去看望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时人们习惯简称为“青艺”)的导演石羽先生,张逸生、金淑之夫妇。石羽是四十年代的经典影片《小城春秋》的主演之一,张、金夫妇早在抗战时期就活跃于重庆话剧界,曾参加了郭沫若的话剧《屈原》的演出。从此,我与他们开始有了往来。来往最多的是张逸生金淑之夫妇,他们所住的青艺宿舍,在东单三条的一个不规则的四合院里,离《北京晚报》很近,我成了他们家的常客,有段时间几乎每周都去吃饭。院子里住有好几家,记得都是青艺的人员。我去的时候,常常能碰上他们在一起聊天。
青艺是文怀沙工作过的地方,自1953年调入,到1963年底入狱,前后达十年。正是从青艺老人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文怀沙”的名字,以及他的一些事情。我随后认识的萧乾、文洁若夫妇,与牛汉先生一样,都是文怀沙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从他们那里,同样听到过关于文的事情。
也很巧,那时我与卞之琳先生也有了往来,他的夫人青林即文怀沙的前妻、文斯先生的生母。我先是为研究巴金和撰写《萧乾传》而去采访卞先生的,后来,编辑“五色土”副刊时,又请他新开“居京琐记”专栏写稿。他寄来的第一篇稿件是《漏室铭》,是为他们的房子遇到麻烦而呼吁的。他们住在干面胡同中国社科院宿舍的顶楼,每遇下雨,房顶就往下漏水,夫妇俩不得不四处用脸盘接水。卞先生文章不温不火,改“陋室铭”为“漏室铭”,把窘状描述出来,令人同情与焦虑。文章发表后,有了很大反响,我当即与房管部门联系,他们也马上派人去楼顶重新铺沥青,从此,卞先生一家不再有漏雨之虞。为此事,卞先生专门来信致谢。也是因为这一缘故,我去他们家的次数也更多了,我们的通信也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先生的文章手稿与书信,我珍藏至今。
后来,从一些文学界的前辈那里,知道青林很有才气,写过小说。自然,他们也谈到过与文怀沙相关的一些事情,如青林如何不能原谅他在她怀孕和坐月子期间做了某件事,才决定离婚……
因此,可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文化界,文怀沙其人其事广为人知,根本不需要刻意打听。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经公开,使人有“爆料”之惊。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这些事情,大多避而远之,当时的许多文化界活动中,也就很难见到他的身影,这一点,查阅当年的相关报道即可得知。
虽然知道其人其事,但我从没有想到要写出来。第一,他不是我所关注的对象,我在情感上一直排斥他,从来没有把他视作一个文人;第二,在我看来,这属于个人品行,是受害者与法制部门管的事,何况他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不过,虽然我没有公开写到他,但我在自己所能影响的范围里,却尽量不让媒体朋友报道他。几年前,《南方都市报》记者来北京做一个文化老人系列采访,请我帮忙联系周有光、杨宪益、王世襄、黄苗子、黄永玉等,名单上本来还有文怀沙,被我毫不犹豫地淘汰。吉林卫视有个《回家》文化纪实栏目,专门拍摄文化界名人与故乡、母校的关系,从一开始我就担任这个节目的艺术顾问和策划,一次,制片人曾去联系过文怀沙,但我坚决反对:“这个系列里,不能有他。”很高兴,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
这便是我二十多年来对文怀沙先生所采取的一贯态度。
二,十年来怀疑其真实年龄
开始怀疑文先生的真实年龄,是在最近十年,其间他的名头越来越大、媒体曝光率越来越频繁,他已不再是二十年前的那个形象,而俨然已成显赫的公众人物。对其真实年龄产生怀疑,主要源于多年来我与一批“二流堂“老人的交往。
“二流堂”是一特殊的文艺家群体,最初形成于1943年抗战期间的重庆,主要人员有唐瑜、吴祖光、吕恩夫妇;金山、张瑞芳夫妇;高集、高汾夫妇;戴浩、盛家伦、方菁、萨空了、沈求我等。经常来此的则有丁聪、黄苗子、郁风、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冯亦代等人。而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夏衍,被他们尊为主心骨。
五十年代初期,“二流堂”中的大多数,又相聚北京,开始几年一些人就住在东单栖凤楼的一个院子里,是为“北京二流堂”。栖凤楼往西,是青艺大院,往南又称西观音寺,与长安街相交,对面即是目前《北京晚报》所在地。
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与“二流堂”中的不少老人有不少来往,写过其中的黄苗子郁风的传记,写过丁聪、冯亦代、吴祖光、夏衍等人的画传或评论,还为有的人整理过日记和书信,对于他们的为人和历史,应该说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近二十年来,这些老人经常不定期聚餐,除“二流堂”老人外,还有杨宪益、王世襄、范用、华君武、姜德明、沈昌文、邵燕祥等。随着一些老人的逐渐飘零,这一聚会的规模越来越小,但在2008年秋天黄苗子先生住院之前从未中断。
据我收藏的一份“文革”初期批判“二流堂”的小报专号,文怀沙也被列入“二流堂”成员之中,对他的介绍是“文化流氓、坏分子、六四年被捕入狱”。文怀沙在五十、六十年代的确与“二流堂”有过来往,但并无过深关系。他们的回忆文章,或者闲谈,从没有正面提到过文怀沙,更不用说叙述彼此之间往来故事。相反,如在闲聊中谈到此公,他们从来都是一种鄙视口气。对于近十年来文怀沙忽然间声名雀起,并被各种媒体冠以“大师”或者“风流”的称谓,“二流堂”健在的老人们颇感意外和惊讶。他们感叹时代变了,对人的评判标准也变了。但是,如果有什么媒体将他们与之相提并论,他们还是会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譬如,前年,某电视台录制一组文化老人节目,分别有文怀沙、黄苗子等,黄苗子获知后,颇感无奈,不住地说:“真要命,怎么把我和他摆在一起了?”
不限于黄苗子,与“二流堂”关系密切的黄永玉,也对文怀沙持鄙视态度。2006年春节,我所在的报纸的文化新闻版发表黄永玉所画狗年生肖漫画,同时还发表了文怀沙的迎新文章,并将两者加框放在一起。黄先生的画是我约来的,遂将报纸送去,他一看,只对我说了一句:“李辉,我该夸你还是骂你?你们怎么把我和文怀沙放在一起了?”几天后,文化新闻版的编辑告诉我,文怀沙看到报纸后,也说了一句话:“哦,黄永玉呀?我们是老朋友了。”
关于文先生的年龄,也是我与这些“二流堂”老人聚会时谈到的话题。有几位老人的出生年份为:唐瑜,1912年;黄苗子,1913;丁聪,1916年;郁风,1916年。属牛的黄苗子先生今年96岁整。他们的疑问是:文怀沙本来比我们小,怎么现在比我们大了呢?
不过,这一怀疑,大家都是饭桌上议论议论而已,并没有想到要公之于众。
三,两年前决定追寻真相
我决定追寻文怀沙的真相,源于两年前的一次刺激。2007年,在郁风老人4月去世后不久,吉林卫视“回家”栏目的制片人李冬冬女士来看我。如前所述,她告诉我,她曾去找过文怀沙,想拍一个他的专题节目,当然我不赞成。谈话中,她告诉我去见文的过程。她说,她介绍这个栏目曾经拍摄过黄苗子、丁聪、郁风等,文一听,马上就说:“哦,我和郁风是好朋友。干校时候,她还找过我,为我画裸体像呢!”
我一听,脱口骂了一句:“王八蛋!”我告诉冬冬:“不可能的事情。文革期间郁风一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不可能去过干校!文怀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写过郁风老人的传记,总是以“老太太”称呼她。郁风的父亲郁华是民国大法官,叔叔郁达夫是著名作家,他们两位在抗战期间先后被日本侵略者所杀害,是有名的民族豪杰。郁风正直,坦诚,甚至天真,她从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经历炒作自己,在我们的聚会中,她永远是一个中心,以率真和爽朗的笑感染大家,为大家带来快乐。她的去世,令我们感到难过不已,没有了她,聚会也从此少了热闹。
这样一个让我敬重与怀念的老人,这样一个在“文革”期间真正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遭受七年磨难的老人,刚刚去世,却让一个因“诈骗、流氓罪”入狱、自称也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人,泼上一盆污水,她的在天之灵一定不会安宁!对如此卑劣之人,我决不能原谅!决不能漠然视之!
这就是我决定要公开质疑的一个最直接原因。它关乎个人感情,也关乎对历史的敬畏。同时,也是本人楚人性格所致。有的读者根据我的文字,只知道我是一个温和、行文节制的人,他们不知道,在生活中,我有时也是一个倔强、固执甚至不给人留情面的人,周围的同事和朋友,深知这一点。
四,今年元旦,决定公开质疑
两年来没有停止追寻,所搜集到的史料和佐证,越来越证明文怀沙的自述与光环——年龄、入狱原因、文化地位等——都存在诸多疑点,必须公开质疑,找到真相。2009年元旦前后,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使我决定撰写《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他》一文。
元旦之前,我所就职的报纸,连续两天刊登整版广告,突出推广“百岁国学大师文怀沙主编”之大型套书《四部文明》(每套售价数万元),声势之大,让人惊叹。我和报社一些同仁,中午常常在编辑部咖啡厅喝茶聊天,那几日,我们谈的是文怀沙其人其事:他的历史陈迹,近年的声名鹊起,特别是他如何已经被成功地“包装“为“国学大师”。显而易见,成为“国学大师”之后,他不仅自己四处题字、演讲带来经济效益,随着一套据说要取代《四库全书》的一套书的推广,将一方面牟取更大经济利益。
《四部文明》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不在我的评价之列。但是,由一个有历史劣迹且又编造个人历史的“国学大师”领衔主编,无法让人接受。报社同仁鼓励我,一定呀把自己的追寻与质疑尽快公布于众。他们说得好——不能让文怀沙 认为神州无人;不能让世人认为媒体中的人都失去了良知;不能让后人笑话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化人都失去了道德标准和勇气。
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与催促下,我在春节之后完成了这篇质疑文章,并请这些同仁分别从法律、史学、文字表述等方面帮忙把关。可以说,质疑文章虽系我个人所写,但从另外角度说,它也是一批媒体人的情感与思考的集中体现。在此,我深深感激他们帮我完成了一个夙愿。
五,我们失去了文化判断力和敬畏吗?
不到十年,文怀沙忽然间被媒体和社会制造成“国学大师”,足以令人们深思之。
中国曾经历政治运动频仍、“知识越多越反动”、“大破文化命”的年代,那时,陈寅恪、梁漱溟、陈垣、冯友兰、钱锺书、沈从文等堪称文化大师的人依然健在,但我们顾不上珍惜和呵护,却让他们不断地写思想检查,进而在放羊、种菜的劳动中消磨生命,这对于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发扬光大,实在是巨大的历史遗憾。
随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变化和国力增强,人们对文化越来越热爱,对文化人也越来越敬重,投资文化的兴趣和实力也越来越大。随之,对文化大师的出现,也越来越渴望。特别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希望借弘扬“国学”而增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努力,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怀沙才有了被“塑造”成“国学大师”并以此获取最大利益的可能与空间。
各界人士对文化老人特别是“国学大师”的尊敬、爱戴的情感,无可厚非;不明真相的人们轻信一个被称作“国学大师”的招摇撞骗、欺世盗名也可以理解。问题是,我们的时代为何失去了文化判断力?为何失去了对大师这一称号的应有的敬畏?在“娱乐至上”的时代,我们的媒体向观众和读者推介一个“国学大师”时,竟显得如此草率,似乎不假思索,不做研究,不要起码的学术评判标准,就可以把“大师”的桂冠轻易地戴在一个人头上,而不管对公众和历史的责任,而没有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具有的文化敬畏。
质疑文怀沙真相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超出我的预料。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我们的公众多么需要历史真相,多么需要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师,多么需要真正对得起后人的文化成果!
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质疑文怀沙及其反响,仅仅成为媒体的一次狂欢,之后,谁都顾不上反省,又一切归于原状。不管怎样,我的任务已经完成。除非有必要,我不再就此事撰文发表新的意见。我将回到既有的写作计划中。更多真相的追寻,可以由有兴趣的其他记者根据相关线索去完成。
2009年2月24日,于北京
| < Prev | Next > |
|---|
- 2011-05-06 -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悲秋题材与文人心态
- 2011-01-23 - 坦然面对死亡 - 大同历史名人李少兰
- 2010-10-09 - 光明日报:东西美学的邂逅——中美学者对话身体美学
- 2010-09-16 - 大自然之歌
- 2010-08-19 - Great Master of Macro History, Mr. Ray Huang
- 2010-02-14 - 老不糊涂:羽扇纶巾叶剑英不乱情场定乾坤
- 2009-12-12 - 成功靠天靠地靠自己(俞敏洪)
- 2009-06-25 - 绿坝系统提醒你,以下内容包含不良信息(韩寒)
- 2009-06-24 - 廖氏愤青教材(转载)
- 2009-05-03 -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摘选)